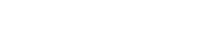2004年6月22日,青藏铁路建造又迎来一个路程碑――西藏段开端铺轨,西藏行将离别没有铁路的前史
。青藏铁路再次成为世人重视的焦点,作为现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穿越多年冻土路程最长的高原铁路,其“冻土攻关”更是备受瞩目。有经历的人指出:“青藏铁路胜败的要害在路基,路基胜败的要害在冻土。”近来,记者造访了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讨所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我国是世界上第三大冻土大国,有75%的国土面积呈冬冻夏融的周期改变。土体在冻住的状况积会发生胀大(冻胀),到了夏日,冻土消融会发生下沉(融沉)。冻土的冻住和消融替换呈现,对在冻土地基上进行工程修建提出了严峻应战。
中科院兰州分院院长、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程国栋院士介绍说,冻土问题,一向被认为是建造高原铁路的一项世界性难题。由于冻土体易发生冻胀和融沉效果,这对路基、桥涵以及地道工程的损坏是相当严重的。如,俄罗斯1994年查询标明,20世纪70年代建成的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其线%;运营近百年的第一条西伯利亚铁路1996年查询的线年查询标明,青藏公路其时病害率达31.7%,东北多年冻土区铁路病害率高达40%。
据了解,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段全长1142公里,海拔4000米以上地段长度约为965公里,要穿越接连多年冻土区632公里,这是现在世界上穿越多年冻土路程最长的高原铁路。其间,穿越年平均地温高于 1.0℃多年冻土区275公里,高含冰量多年冻土区221公里,高温高含冰量堆叠路段约为134公里。在工程的效果下,这些多年冻土极易发生显着的改变而发生消融下沉问题。
中科院常识立异工程重点项目“青藏铁路工程与多年冻土相互效果及其环境效应”项目首席科学家马巍研讨员介绍说,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咱们进一步研讨了新的地温调控原理和高新技能,经过调控辐射、对流、传导等办法,为多年冻土区提出了相应的修路技能:块石路基结构、通风管路基、热棒 保温材料结构办法、遮阳板办法等。
在中科院青藏铁路北麓河实验段演示工程现场,记者还看到一种全新的“热棒 保温材料结构”办法:在冻土路基的两旁插着一排排直径约15厘米、高约2米的铁棒。同是“青藏铁路工程与多年冻土相互效果及其环境效应”项目首席科学家的吴青柏研讨员介绍,这便是热棒。热棒是一根密封的管,里边充以工质(如氨、氟利昂、丙烷、CO2等),管的上端为冷凝器(由散热片组成),下端为蒸腾器。当冷凝器温度不高于蒸腾器的温度时,蒸腾器中的液体工质吸收热量,蒸腾成汽体工质,在压差效果下,蒸汽上升至冷凝端,放出汽化潜热,再经过冷凝器散热片散出。一起蒸汽工质遇冷冷凝成液体,在重力效果下,液体沿管壁回流至蒸腾段,再蒸腾。如此往复循环,将热量传出。
“青藏铁路建造承载着几代科研人的愿望和汗水!”程国栋院士慨叹地说,“为了了解和处理青藏铁路多年冻土问题,科研工作者几十年如一日,从始至终坚持在条件极为恶劣的高原环境里做科研。”据介绍,40多年来,中科院原冰川冻土研讨所(现合并到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讨所内)的科研人员简直参加了我国在冻土区一切的严重工程建造。正是一批批科研人员忘我支付,为处理青藏铁路建造中严重冻土技能难题积累了名贵的第一手资料。
高寒、缺氧的恶劣环境还造就了一支勇于喫苦、不畏艰难、乐于贡献、身手过硬的科研部队。采访中,记者听到许多感人的科研业绩。程国栋院士,这位受人敬重的世界闻名冻土专家在青藏高原一扎便是40年。一位科研人员回忆起与程国栋院士进行户外调查的情形说:“在人迹罕至的青藏高原,种种窘境连咱们这些土生土长的西北人都习惯不了,而他一个南方人却一点点没有畏缩。”